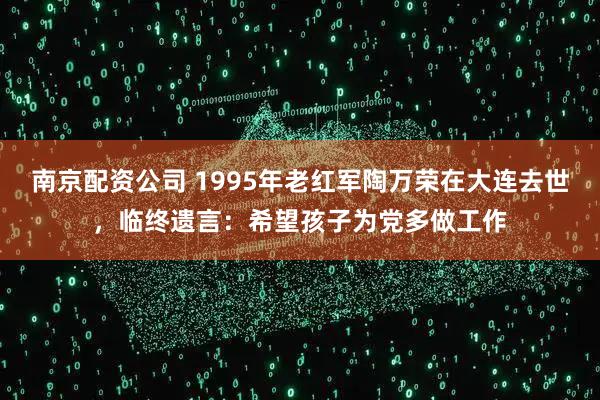
“1995年12月30日晚上九点,你们一定要替我把名字改回来。”病房的灯光很暗南京配资公司,87岁的老人握着护士的手,一字一句。她的身份证写着“苏风”,可在党史档案里,她更响亮的名字叫陶万荣。

冬夜的海风穿过大连的街巷,医院窗外隐约能听到汽笛声。熟悉陶万荣的人都明白,她执意改名,不是出于荣誉,而是要把那些被尘封的岁月交还给组织。几十年里,“苏风”只是工作需要的伪装,“陶万荣”才是那位在祁连山浴血、在通江高歌的女营长。
在中国革命年代,改名并不稀奇。王平、李德胜(毛泽东的化名)都是如此,但陶万荣对本名的坚持显得别样固执。原因很简单——这是她与八万川陕子弟兵共同拼杀、与一千多名女兵同甘共苦的见证。名字丢了,似乎连牺牲的姐妹也会被忘记。
时间拨回到1933年初春。通江县城外,红四方面军把招来的四百多位女青年编为妇女独立营。17岁的陶万荣个头不高,却被徐向前点名当营长。有人窃窃私语:“黄毛丫头能带兵?”结果,她用一次夜袭给出了回答。举着扁担的女兵们悄悄摸上鹰龙山,拦腰截住了田颂尧部的一个团。第二天清点,俘虏数百,枪支弹药堆成小山。总部决定:缴获的武器全部留给独立营,用不着上交。

这一仗打出威风,也打出了信心。没多久,苍溪、长赤、广元纷纷照葫芦画瓢,组建自己的女兵连、女兵营。有人说,这些姑娘不过是抬担架、送军粮的“后勤队”。事实恰恰相反——川陕按计划把侦察、破袭、掩护等硬活都塞给了她们。陶万荣常说:“别把我们当花瓶,打起仗来,我们一样要掉脑袋。”
1935年6月,她跟着独立师到懋功会师。庆祝会上,她抡起马刀又唱又跳,毛泽东在后台连声称赞:“好一个黄毛丫头!”那顿由陶万荣掌勺的野菜面,让主席记了一生。可惜快乐没能持续太久。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,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成了日后惨烈的西路军。

祁连山脚下的冷风像刀子。妇女抗日先锋团——1300多名平均不到20岁的女红军——被马家军分割包围。弹尽援绝后,部队被迫分散游击。陶万荣带着十几名姐妹在山林里硬撑,昼伏夜行,饥寒交迫。一个夜晚,她们点火取暖被敌人发现,只得毁掉党员证,拼尽最后体力。结局众所周知:大多数被俘,几位主官甚至自尽殉节。
被押往南京反省院的路上,陶万荣咬破手指,在衣袖里写下两个字:“活着。”一年多后,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,周恩来、叶剑英把她们营救到延安。别的同志选择休养,她却主动请缨:“我还要打仗。”1941年,经批准,她改名“苏风”奔赴山东抗日前线,再没人提“黄毛丫头”。
自山东到东北,她先后干过公安、后勤、武装工业,岗位换得快,名字却始终没变回来。抗美援朝结束,她留在大连的112厂当副厂长。有人劝她写回忆录、申报军衔,她摆摆手:“新任务多得很,写什么传记?”1958年,毛泽东途经沈阳,专点名要见“黄毛丫头”。她匆匆赶到,做了顿家常菜,主席笑道:“味道还是当年的味道。”二人不再提战火,只聊起工厂产量和技术革新。

1955年授衔那年,不少同批女红军因为转业无缘军衔。对此,她看得很淡:“干什么不是为人民?肩上的星星是对同志们的肯定,但不是评价一生的秤砣。”在她眼中,比星星更沉甸甸的是烈血滩无名女战士的坟冢。
1993年,她第一次住院,硬撑着写下一段话:“我们没荒废日子,也没给党添乱;不图碑,不图章,有这把老骨头就行。”字迹歪斜,却句句铿锵。其实她早知癌细胞在扩散,却吭都不吭一声。

1995年12月31日零点,心电监护仪划出最后一条直线。家属守在床边,她只留一句话:“我两手空空参加革命,清风两袖离开世界,能留给党的只有七个孩子,让他们多干点事。”简单得像命令,也像托付。
噩耗传到北京,罗荣桓夫人林月琴、刘伯承夫人汪荣华等几位老革命握笔颤抖,写下“长征老战友,红军女英雄”的挽联。陈慕华批注:“红军女杰”。字不多,却分量沉。
二十多年过去,很多人仍只在通江纪念馆的玻璃柜里,与那件被烟火熏黑的军大衣、那只缴自日军的柳条包相遇。2021年,通江县派人来大连,子女们把母亲的遗物悉数捐出。交接时,老大陶卫东说:“妈常讲,东西属于组织,我们只是暂管。”

不得不说,世人记住的常是将帅的闪光,容易忽略汗水与苦难的暗角。陶万荣这一代女红军,用生命撕出了一条缝,让后人看见女性在中国革命中的直接战斗角色,而不仅是“战地黄花”。她未曾捞过半点个人好处,却把一生重量压在“希望孩子为党多做工作”这句话上。倘若今天有人走进烈血滩,抬头读那无名女兵的碑文,大概能明白老人为什么坚持要把真名写回档案——那不是个人符号,而是一段历史坐标。
盈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