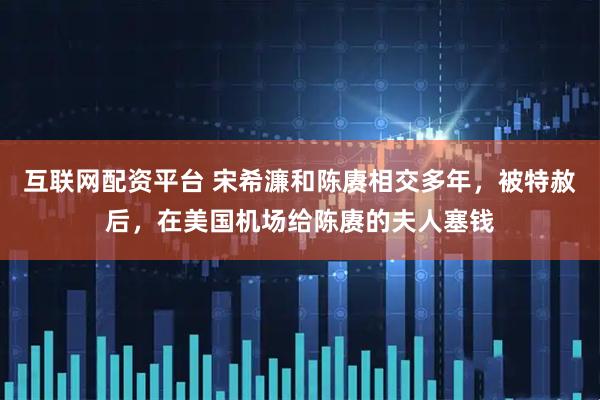
“傅大姐,这点心意您务必收下,好让我在老朋友面前少一分愧疚。”——1985年10月互联网配资平台,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候机长廊里,七十七岁的宋希濂把一沓美元塞进傅涯手中,又低声补了一句,“回去替我给陈老总磕个头。”对话只持续了十几秒,却像一支火柴,将半个世纪的恩怨与情谊照得通亮。
那一年距陈赓去世已整整二十四年。傅涯原想婉拒,无奈宋希濂执拗得很,只得收下。送走航班后,老人靠在栏杆边,久久没有离开,西岸微咸的海风里,他想起两个人从黄埔操场到战火硝烟的全部往事,胸口一阵闷疼——此生最后一次“见”老友,只能托付在薄薄几张纸币上。

把时间拨回到1923年的初秋。长沙到广州的邮船上,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赓背着一只土色帆布包,站在甲板最前端。他抽空向同船旅客拉家常,听到身后那口浓重湘乡腔,循声一看——是宋希濂。两人同乡,一路有说有笑,谈理想、谈军阀混战,也谈长沙米粉的辣味谁家最好。短短几天,便成莫逆。
广州登陆后,两人本该进入程潜的讲武学堂。可陈赓摸到消息,说孙中山正筹一所新军校。他拍拍宋希濂的肩膀:“去黄埔,赌一次大的!”宋希濂憨厚却爽快:“听你的。”于是双双递交报名表,成为黄埔一期学员,一个分在第三队,一个被编进第十队。
黄埔课堂紧凑,操场更残酷。陈赓身体灵活,加之天生外向,很快成了三队骨干;宋希濂沉默寡言,但射击成绩首屈一指。课堂外,两人常在珠江边散步。陈赓讲革命理论,描绘“军人也能做大文章”;宋希濂则琢磨“战场怎么活”。同窗数月,性格互补,却惺惺相惜。周恩来第一次在礼堂报告国际形势时,宋希濂还趁热闹挤到陈赓旁边,小声问:“这位周主任,看着年轻,底子深吗?”陈赓咧嘴笑:“日后你就知道。”

1925年东征期间,两人首次并肩实战。陈赓夜袭棉湖桥,宋希濂负责侧翼掩护。战后营地里,陈赓递来半壶凉酒:“大头,干了!”宋希濂喝完,憨笑不语,心里对这位“主意多的大哥”更加佩服。可好景不长,中山舰事件骤起,黄埔气氛转冷。宋希濂身份尴尬,给陈赓写信自嘲“风向不辨”,却迟迟未得回音。国共裂痕扩大,他终究投向蒋介石,改穿青天白日帽徽。再见面,一个是地下党要员,一个是国民党上校,剑拔弩张又心怀牵挂。
1936年西安事变后,两人终于在古城重聚。宋希濂设席,全桌黄酒热气腾腾。陈赓说自己被捕时蒋介石许以高官,他拒绝;又说抗日大势刻不容缓,大家应把枪口对外。宋希濂听得脸色复杂,端起酒碗:“我若能决定,就不打内战。”一句话既是应承,也是无奈。那夜他们喝得酩酊,却谁都明白,再握手,必在战场。
抗日全面爆发,宋希濂在淞沪、兰封、富金山连打硬仗;陈赓则在太行山布下游击纵队。不同阵地,同样流血。一次冀中电话线被截,陈赓在军用地图边叹道:“如果宋大头的人马在这里,就能顶一顶。”副官愣住:“那是中央军啊。”陈赓摆手,“打日本人时,不分红白。” 这话被身边记录员写进日记,后来在审讯战犯时被翻到,宋希濂读后沉默良久。

1949年冬,川西公路泥泞。宋希濂指挥的西南兵团被解放军合围,弹尽粮绝。参谋建议突围,他咬牙放下望远镜:“无意义,不再牺牲弟兄。”被俘的第一晚,他躺在木板上,回想二十多年军旅,心中只有一件事最沉:该如何面对陈赓?不久,陈赓专程前来看望。门一推开,他笑着喊:“宋大头,还认得我吗?”宋希濂踉跄起身,两人隔桌握手,泪水夺眶。陈赓没提立场,只问身体,又叮嘱“放下包袱,好好学习”。走前还把自己随身的毛毯留给宋希濂。那晚,宋希濂在灯下写心得:“当记陈兄一片大义”。
1959年,宋希濂获得特赦,搬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没人规定他必须去干什么,可他主动报名到河北新乐人民公社劳动。拿锄头、灌麦田,瘦弱却卖力,有人好奇:“宋将军图个啥?”他苦笑回答:“过去弄坏的,总得补点儿。”同年底,中央聚黄埔老同学,患癌的陈赓拖着病体赶来,合影时支撑不住,只好靠在宋希濂胳膊上。散步那段小路,冬草枯黄,宋希濂扶他走得极慢。谈话内容外人不知,只记得两人都笑着,像回到珠江边的夜色里。
1961年3月,陈赓病逝上海。讣告见报,宋希濂正随基建工程队在东北。听到噩耗,他当场脱帽默立,随后向上级请假赶赴追悼会。灵堂内,他抬头望挽联,双膝一软,差点跪下。人群搀起他,他仍握着花圈不放,嘴里喃喃:“老陈,我来迟了。”

之后二十余年,宋希濂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去湖南、去云南讲抗战史料,凡被批准,他总把陈赓的战例放进课堂,甚至比讲自己还详细。有人提醒“淡些个人感情”,他摆摆手:“那不是感情,是历史。”
1985年傅涯因探亲赴美,宋希濂已在洛杉矶与子女同住。听说老友遗孀到来,他包下一辆租车,亲自接机,陪同逛博物馆,看海滩,再请吃湖南菜。临别那晚,他提前备好一个信封,里面除美元外,还有一张黄白相间的旧照片——黄埔大操场,两个青年肩并肩,笑得极响。宋希濂塞钱时还把照片一起递过去,声音沙哑:“照片您带回去,钱就算给老陈买一瓶好酒。”
航班起飞后,宋希濂在空旷大厅坐了许久。旁边一个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落泪,他捋起袖子指着肘上斑驳旧伤:“当年富金山,中弹的位置。给我包扎的救护兵,学的就是陈赓的战场救护条例。要不是那本条例,我早就没命。你说我该不该感谢他?”话说到一半,手指微微颤抖,却依旧挺直脊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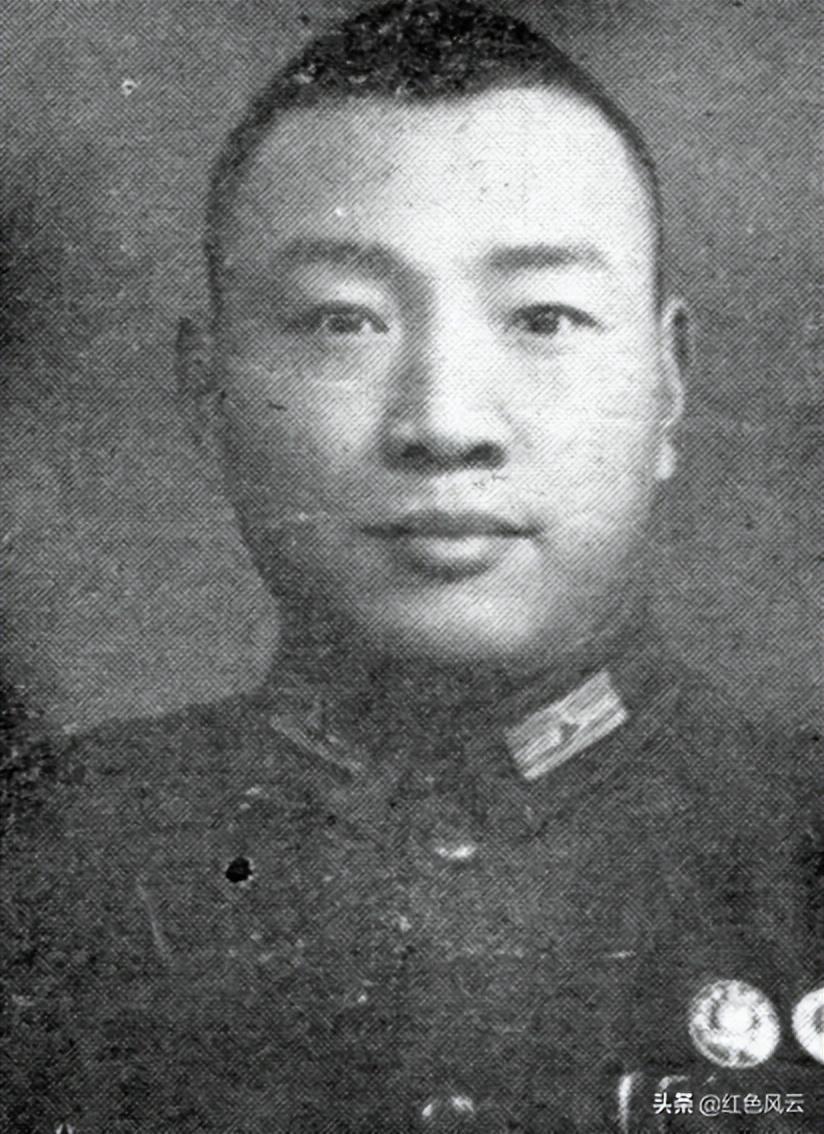
1990年代初,宋希濂回国定居,先到八宝山祭奠陈赓,再去湖南老家。墓前,他一言不发,只把当年那张相片重新塑封,放进花束中。后来他接受电视台采访,被问及此生最大遗憾,他沉吟片刻:“解放前若能听进他三句话,或许会更早为国家效力;不过人生不能重来,只能尽力把后半段走正。”
这句话说完,他不再评价个人抉择。面对镜头,他更愿意强调黄埔同学共同的血性与抗日功绩,又特别提醒主持人别忘了提陈赓:“他是真正懂战争,也懂人心的人。”
2006年,宋希濂溘然长逝。整理遗物时,子女发现一本磨破的黑封笔记本,扉页写着八个字——“陈兄在上,吾当自砺”。旁边夹着两张机票存根,起始地洛杉矶,终点北京,日期正是1985年10月。纸角泛黄,却依稀带着那天机场的海风味。

回顾这一段跨越六十余年的交情,外人最难理解的是:一个终身忠于共产党,一个曾被视为蒋介石的嫡系干将,何以在分裂与拼杀的年代仍保持敬重?答案或许隐藏在他们第一次并肩作战的夜里——枪声停歇,火光渐暗,两位湖南青年蹲在堑壕边,你递我一口冷饭,我递你一块干肉。命能相托,情自难断。战争可以拆散阵营,却拆不掉见过彼此血与汗的人;政见可以左右道路,却左右不了真诚和担当。
正因如此,宋希濂在美国机场那一次“塞钱”,不只是一个老兵的私人礼数,更是一种迟来的致敬:敬那位始终一腔热血的兄长,也敬两代黄埔人无可置换的悲欢。
盈富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